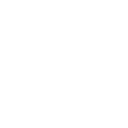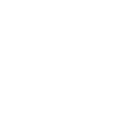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说:“儵鱼在水中从容地游动,这是鱼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如何知道鱼的快乐的?”
庄子说:“你不是我,又如何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的感受;但你固然也不是鱼,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就是肯定的了。”
庄子说:“请顺着开始的地方想。你说‘你如何知道鱼的快乐’,就是在你自己知道了我知道鱼之乐之后问得我。而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
在故事中,庄子看到鱼游得从容,感觉鱼是快乐的。惠子则怀疑庄子知道鱼之乐的可能性。庄子首先用了一个反问:“你又不是我,如何知道我知不知道呢?”。惠子在随即的回答中,先承认自己不是庄子也就不了解庄子的感想,又进一步认为,庄子不是鱼也就不知道鱼的感想了。但庄子在故事的最后既肯定了他自己知道鱼的快乐,又肯定了惠子知道庄子能体会到鱼的快乐。
由此可见,庄惠的争论主要针对的是人与鱼、人与人互相感受,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平时是如何理解他人的呢?当我们最初与外界接触时,我们的经验是原始的,并不能分清什么是外界,什么是“他”,什么又是“我”,这时外部事物与“我”之间不存在一条界限。只有当我们经历过后回想,才会逐渐发现刚才的经验是“我”的经验,而经验的对象——触摸的物体、对我微笑的人、一条在我面前游过的小鱼并不是“我”。由此,我认识了作为经验主体的“我”,以及外界即“时空中的对象”。
在此之后的对经验的反思中,我们将逐渐形成越来越准确的概念来把握外界事物的属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对一条游动的鱼,我们将在脑中留存关于它的形状、它游动的身姿的形象;而且知道它是活的(当然这也伴随着对“生命”这个概念的认识过程),记住它要在水中活动,最后再用语言中“鱼”这个词来代表、指称这种存在的物。
但如果一直沿着这条思路去认识“鱼”,我们就只能永远和惠子一样了,即认为“它是,而且也只能是一条鱼。”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关于鱼的生活习性的知识甚至解剖知识,但却永远不可能觉得“它很快乐”。因为在我们看来,“鱼”和“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只能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出现在“我”的对立面上,而不会和我的生命产生联系。
庄子又为什么能像小孩子一般说出“小鱼真快乐”呢?这是因为在庄子看来,“鱼”和“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与“我”的生命休戚相关,甚至是“我”的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小鱼与我的关系,并不是“我—它”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你”的关系:“我”不是“你”,也并不占有“你”,但“你”一直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存在于“我”的生命中,由此组成我的生命,构成了
“我”。于是,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也随即变化,变得与我息息相关,而我也感受到完整的人格。庄子便可以感觉到鱼的快乐,惠子也可以知道庄子知道鱼的快乐了。
至于小孩为什么比成人更有可能说出“小鱼真快乐”呢?我想是因为小孩与成人相比,对经验的对象还没有形成较完善的概念,没有将我与对象完全看作是本质不同的两者(概念既是把握事物属性、本质的工具),即“我”与“它”还没有完全被区分开来。如此,也就有比成人更多的可能去感觉到鱼的快乐了。
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荡荡,十分轻松惬意。他这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周。过一会儿,他醒来了,对自己还是庄周感到十分惊奇疑惑。他认真的想了又想,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庄周与蝴蝶一定是有分别的。这便称之为物我合一吧。
大意:庄子和惠子在桥上游玩,庄子说:“鲦鱼游得从容自在,这是鱼的快乐呀。”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快乐。而你也不是鱼,那你肯定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从最初的话题说起。你说‘你在哪里(安:一意为如何,怎么;一意为在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既然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还问我?我是在桥上知道的。
鲁人身②善织屦③,妻善织缟,而欲徒于④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⑤之也,而越人跣⑥行;缟⑦为冠之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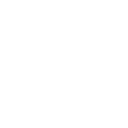

@BETHASH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