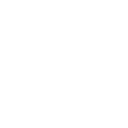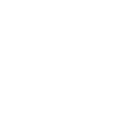“鱼之乐”也好,“死之乐”也好,都是当“我”与他者建立深入的关系,沉浸并享受着同一个这个世界的时候,所窥见的经验。享受“鱼之乐”“死之乐”的时候,“我”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活在一个鱼儿欢快畅游的世界,活在一个妻子死后的世界。
在“物化”之中,首先事物应当绝对满足于各自的处境(“此”),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乍看起来,这似乎形成了一个自同者(与自我同一的相同事物)的闭环,又如何能够变为他物, 构成不同的世界(“彼”)呢?我想在回顾前述讨论的同时,对其加以说明。
对于以“道”——超越论的原理——作为根据的宇宙,“物化”这种变化在其上凿出了窍穴。因为“这个我”在作为“这个我”而存在,与此同时,也能变成完全不同的其他事物。如此,本质的同一性则被瓦解。而且,从超越论的视点来看待万物流变——这一以往的“齐同”观中,“物化”不过是“这个世界” 中的种种化身(avatar),但如果能看到在“物化”之中,不仅是“这个我”,连“这个世界”也能变化——这一根本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作为超越论原理的“道”,其自身也是能够变化的。
但是,话虽如此,既然在变化后的他物之中,“这个我”与“这个世界”被重新组成,那么最终他者及他世界会不会并未打开,而不过是改换了内容的自同者闭环呢?
为了思考这一问题,我想在本章讨论《庄子》中的他者问题,这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物化”的思想。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这里要谈的是《庄子·秋水》篇末,惠子与庄子围绕“鱼之乐”的论辩。虽然仅为一百余字的片段,却像本书开头所言,连汤川秀树也对此问题有所关心。可以说这一古老论争回响,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知识界的最前沿。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一论辩由两种逻辑所构成。其一,是惠子所主张的逻辑, 可以将之概括为“他者经验不可知”。可知的只能是自我的经验。自我的经验具有隔绝于他者的固有性,他者不可窥知。在此,我想将其称为“tautology”(ταuτός +λόγος =同一自我的逻辑)。
然而,想将这一逻辑贯彻到底,原本就不容易。因为既然是逻各斯,那么必然一直会对他者开放交流的大门,其逻辑本身应该能被他者所知晓。同时,作为前提的虽说是“同一自我”,但其身份却是不稳定的。这指的究竟是这个世界中为数众多的“自我”中的一人,还是构成这个4 4 世界,不可替代的作为中心的自我?而且,这里所说的自我经验的固有性,究竟是指怎样的固有性,也值得讨论。这是指,自我所认知的“天空之蓝”与他人所认知的内容有绝对的差异——这一意义上的内容的特殊性吗?还是说,“蓝”这一概念既然可以普遍化,则可以与他者的经验相交流——这一意义上的固有性吗?不禁涌现出种种疑问。
那么,庄子是在何处,以怎样的方式,反驳了惠子的呢?有趣的是,庄子首先通过重复惠子的同一自我逻辑,来对之进行反驳,即“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一处。“他者经验不可知” 的这一命题,既然作为他者的庄子能够将之重复,那么惠子的同一自我逻辑,显然在逻辑上想要躲在自我之中是不可能的。庄子想通过重复同一自我逻辑,让其露出破绽。
不过,讽刺的是,正因如此,庄子反而延长了惠子同一自我逻辑的生命。即证明了惠子的逻辑,是能被他者所维持、所延续的强有力的逻辑。因而惠子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
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通过再次重复来回答庄子。这显示出惠子的同一自我逻辑并非仅属于自我,而且也能被他者所承认。如此,同一自我逻辑超越了自我而得到了扩张。
尽管如此,此处支撑着扩张后的同一自我逻辑的他者,并非作为他者的他者,不过是又一个自我而已。庄子想让自己作为“他者经验不可知”所排除掉的他者来登场,而惠子则将这样的庄子打扮成承认“他者经验不可知”的又一个自我。总而言之, 在庄子与惠子的对话中,看起来他者似乎得以成立,但实际上却被再次抹消了。
而此时,被抹消掉的不仅是他者。由于作为“同一自我”的自我扩张,作为特异性的自我(姑且称作“我”)也被抹消。在此必须思考的是,自我经验的固有性。惠子所设想的经验的固有性,并非只是鱼与人类这种不同物种间,由于经验结构整体差异而产生的固有性。而像庄子与惠子,这种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经验结构的人类,其个体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由于经验内容差异而产生的私密性的固有性。也就是说,所谓“他者经验不可知”,不仅是人类不能通过经验结构的整体差异来知晓人类之外的存在者的经验,而且也不能在内容上获知作为个体的他人的经验。
正因如此,惠子的论说实际上是强而有力的。并且,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惠子把经验固有性的议论,与经验的结构整体差异、经验的内容差异,同时放置在了问题的层面,从而使特殊与普遍得以联系。一方面,自我经验不能被他人所窥知,是私密
然而,自我经验的私密的固有性,并不能尽数涵盖“我”的经验。庄子在最后的反驳,正是试图从具有自我经验固有性的同一自我逻辑陷阱中逃脱出来。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在此,庄子转了一个大弯,即自我经验的固有性,并不在于他人无法窥知的私密性中,而是产生于与他者的亲近关系中。说得重一点的话,如果没有“我”与他者的亲近关系,那么连私密性也无法成立。
首先,庄子把自我经验结构本身作为问题的对象。经验之所以作为经验而成立,是因为其必然向自我之外的事物开放。无论自我经验的建构之处,在多大程度上隔绝于他者,但只要是经验,则在理论上必然暴露在他者之前。而且,在这一场景中,庄子与惠子间达成了某种对话,在形式上,惠子及庄子均应了解其经验是向他者开放的,尽管惠子并不能理解庄子的他者经验的内容。
在此之上,关于他者经验的内容,庄子补充道:“我知之濠上。”也就是说,“我”在濠上这一具体的地方,进入到与鱼的某种亲近关系中,从而知觉到了“鱼之乐”。对“我”来说,“鱼之乐”是十分具体且又直接的,毫无怀疑的余地。
不过,这并不像解释者所说的那样,是“以朴素感性而知”(池田知久《庄子》下,第486 页)。这种知觉并非“朴素”“自然”“自明”的。
眼下此时此处的自我,知觉到某种事物的瞬间,知觉的明证性被知觉的同时性所保证,这几乎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甚至可以说,即使知觉发生了错误,错误的知觉本身,即是明证的,而为了判断错误,亦不得不借助别的知觉。那么,“鱼之乐”可以用这种知觉明证性的机制——将知觉的现在性加以特权化的机制——来说明吗?
不,这并不可行。假如“鱼之乐”,是作为“此时、此处” 的变化——“彼时、彼处”在“濠上”的知觉,以及其明证性的话,那么“鱼之乐”,不过是借由贯穿时间的同一自我,所保证的经验。庄子的反驳,反而变成了对同一自我逻辑的补充。庄子之意显然并非如此,因为“鱼之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知觉明证性被动摇的状态。
关于这一问题,桑子敏雄(1951— )的论说颇有启发。桑子氏首先召唤了作为现代惠子的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 1937— ):
那么,如果是内格尔的话,对庄子将会有以下反驳。即我们的体验是由与鱼的感觉器官完全不同的器官所产生的,因而除了通过自身的体验来想象之外,我们是无法知鱼乐的。也就是说, 对于鱼来说,其无法知道作为“鱼”是怎样的,“鱼”之乐是怎样的。即使认为庄周真能知鱼乐,那也不过是说庄周能够想象变成鱼后,有怎样的快乐而已。
桑子敏雄《知鱼乐——庄子对分析哲学》,《比较思想研究》第22 号,第22 页
对此,作为现代庄子的桑子敏雄,有以下的反驳。虽然篇幅较长,但因其颇为重要,故引用时不作省略:
那么,庄周将如何回答内格尔的反驳?庄周所说的知鱼乐, 其本意又在何处?重要之处在于,庄周是在濠水的岸边知道了畅游其中的鱼的快乐,这并不是说庄周得到了关于鱼的心理的普遍性知识。庄周最后的回答,其重要性正在于此。庄子的认识,体现出被置于特定时空中的身体,及与其有一定关系的鱼
之间的位置关系。这一位置关系,必须在濠水岸边方能成立。惠施从“在所有人类与所有鱼之间,能够知道对方的情感的这种关系,不能成立”这一普遍性命题,推导出“庄周不能知道鱼的情感”。对此,庄周认为,不能用这样的普遍性命题来推导自己是否知道鱼的情感的。“知之濠上”的重要性在于,对于鱼的快乐的认知,是发生在具有身置的体验之中的。庄周的反驳,并非将具体事例作为普遍命题的反例,而是在批判这种在普遍性的“知”的框架之中,思考“知”的思维本身。
庄周与鱼共享着同一环境。庄周的身体,在环境中有其自身的位置。庄周在濠水岸边,眺望江川,观赏游鱼。在这一庄周的环境中,鱼在畅游。畅游的快乐,绝不是仅仅产生于内心的体验。这种体验产生于环境之中。畅游的快乐,发生于畅游者的身体、围绕畅游者的环境(濠水)、庄周身体之中,也发生于三者之间所产生的心理状态的整体性之中。近代性的客观主义,一直将“快乐”这种情感视作内在的、主观的体验。然而,庄周所说的畅游的快乐,是借由感知快乐的主体与引起快乐的外部之间的关系,方得以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将这种快乐,简单还原为内心的体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畅游的快乐”,仅在畅游的主体及其所处环境之间,这种关系并不成立。庄周亲临的环境中,有他者畅游,当这一条件成立时,“快乐”——作为在庄周的身置中,在他者的身体、环境及自身身体中,产生的整体性——方始成立。“畅游的快乐”,是在亲临他者及其环境的庄周的身置中,所产生的他者的快乐。亲临其境,即具有身置。
“畅游的快乐”,是在“具有身置的体验”中产生的, 并非孤立的心理现象。同时,不能像内格尔那样,把对“鱼之乐”的理解,停留在人或自我,将其“主观的”快乐加以变化的事物。桑子想把“鱼之乐”理解为“作为在庄周的身置中, 在他者的身体、环境及自身身体中,所产生的整体性”。而这正是通过“具有身置的体验”所得到的“他者的快乐”。
如此,则“鱼之乐”想要告诉我们的,并非知觉的明证性。知觉的明证性,不过是“主观的”明证性,在特定时空中庄周鲜明地知觉到“鱼之乐”,通过此事,庄周证明了其经验的真切。然而,这里要问的是,庄子这一“主观”或“自我”,在成为前提之前的情况。这并不是说,“自我”事先存在,并与鱼构成特定的身置,在此之上,明证地知觉到“鱼之乐”。而是“鱼之乐”这一全然不同的经验,因为“我”与鱼在濠水的相遇而得以成立。这一经验,既是“我”的经验(而且是深深扎根于身体的经验),同时也是超出“我”的经验(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完全是被动的经验)。
我所说的建立在身置之上的认识,自不用说,并不具有普遍性。即便立于濠水之上,不能知鱼乐者,不知凡几。而较之于知鱼乐者,更多人不知被钓之鱼的苦辛,而耽于垂钓之乐。尽管如此,“知鱼乐”这种认识,并不是作为人类难以认识鱼的情感的个别反证,与普遍相对立。
尽管在濠水看到了鱼,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触发任何思考,便已看过。又或是把鱼视作垂钓的客体,不会去畅想“鱼之乐”。因此,体验“知鱼乐”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并不是在证明“自我”经验的固有性,而是说,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与作为“他者的快乐”的“鱼之乐”相遇,并在相遇中,“我”作为特殊的“我”而成立。存在于这里的,是一种根本的被动性的经验。“我”自身,因为被“他者的快乐”所触发,从而得以成立。
换言之,“鱼之乐”的经验,说的是“我”与鱼在濠水进入到了某种亲近的关系之中。这并不是眼下“此时、此处”的知觉能动的明证性,而是产生于自己跟前的一种“秘密”。这是让“我”与鱼一同感觉到“鱼之乐”,让“我”与鱼同属于同一个这个世界的“秘密”。知觉的明证性,只有在被动性所部分揭露出的这个世界成立之后,方为可能。
让我们再玩味一下桑子所说“亲临其境即具有身置”这一命题。在濠水见到游鱼,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到“鱼之乐” 的经验之中。所谓的“亲临其境”,并不是在其“境”即可,而是当自己被置于某一特定时空之时,要将其作为“境”(当下的处境)来接受。如果没有被动性的接受,那么“亲临其境”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深理解,让我们看看“鱼之乐”之外的例子。这是一种可以说是“死之乐”的情况: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则记述,收于紧接在“鱼之乐”《秋水》之后的《至乐》篇中。如《至乐》的篇名所示,该篇讨论的是快乐的极致。
这则记述同样是庄子与惠子的问答。此处,惠子认为庄子在妻子身故之后,应该哭泣。而庄子在妻子的棺材旁边,非但没哭,还敲起了盆子,放声高歌,显得十分快乐。对庄子来说,这是对妻子的一种供养。也就是说,对于庄子而言,所谓“亲临其境”,不是照例地痛哭流涕,而是与亡妻一同享受“死之乐”。
在“鱼之乐”的讨论中,大多数人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与作为动物的鱼之间,能否共享“快乐”。如果仿照其说,那么我们在此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生者与冰冷无情的死者之间,能否共享“快乐”。然而,这样的提问,并不契合“死之乐”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无论是“鱼之乐”还是“死之乐”,均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他我认识的问题”(桑子敏雄)。庄子记述的,是“鱼之乐”与“死之乐”所凸显出的“亲近”的经验。并不是身故的妻子作为主体知觉到了“死之乐”,而是在庄子与妻子的“亲近”关系中,“死之乐”得到了成立。我们应当思考的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亲临其境”,必须被动地去接受。但仅凭自然、朴素的态度,是难以将“境”(当下的处境)作为“亲近”关系而接受的。那么,为了接受当下的处境,需要有怎样的条件呢?这就是“通乎命”的智慧。
最初,庄子像惠子所期待的那样,为妻子之死痛哭流涕,感到悲伤。然而,当庄子发现这是“不通乎命”时,他停止了哭泣,沉浸到“死之乐”中。也就是说,为了知道“死之乐”,必须有“通乎命”的智慧。关于“通乎命”的内容,庄子是这样说明的:“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 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如果没有“通乎命”的智慧,则很难知晓“死之乐”。痛哭流涕的庄子,由于“亲临”妻子的棺椁之旁,从而发动智慧,得以共享“死之乐”。不过,所谓“亲临其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想通过“供养”一词,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供养” 是大家所熟知的佛教用语,在此我想通过阐明其语源上的意义,从而让我们得到理解的“共鸣”。“供养”一词, 在梵文中, 有pūjā“ 供奉, 尊重, 崇拜”, 或是upa- √ sthā“向…… ;在……的附近;在……下面”“站立;持续存在;依存”等古老的含义。两词均让人联想到面向他者时无可避免的身体上的位置,特别是upa- √ sthā 如其字面所示,有置身于他者之旁,为侍奉他者而存在的意义。upa- √ sthā 在佛经汉译中,除“供养”以外,还被分别译为“住、安住,处,亲近, 起、发起,奉行”。这些词均体现了由于我与他者“亲临其境”, 从而使亲近关系得以成立,产生特殊经验的这一情况。
不过,upa- √ sthā 中也同时潜伏着同一自我逻辑(tautology)。即存在着“我”变为“自我”,并把他者同化为又一自我的危险。作为“安住”的upa- √ sthā,似乎有着与“供养”相反的方向。upa(在……附近)脱落后的sthāna 一词,更能如实地反映这一点。sthāna 有“(财物的)贮藏,完全的寂静,地位,身份,阶级”的意思,佛经汉译中有时会翻译为“法”“义”。
为了议论的进一步展开,这里让我们看一下与upa- √ sthā 相关联的upa- √ ās。这是由upa 与ās(坐,滞留,居住,佛经汉译为“在,住”)所构成的复合词,有“坐在……附近,向……表示尊敬、祝福”的含义。而与upa- √ sthā 相同,upa- √ ās 一般被理解为“坐在……附近”。这里之所以举出upa- √ ās 一词,不仅是因为其与upa- √ sthā 有着相似的意义及结构,而且对于思考upa- √ sthā 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状态,也十分重要。其名词形式的upāsaka(优婆塞)、upāsikā(优婆夷)为我们所熟知。优婆塞、优婆夷是做布施,行供养的在家信徒,区别且脱离于作为教团成员的bhikşu(比丘),是位于周边的暧昧的存在= 边缘的存在。他们“遵守戒律,并为教团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中村元、福永光司、田村芳朗、今野达、末木文美士编《佛教辞典》第二版,第74 页)。具体而言,信徒们照顾出家人的衣、食、住,这正是为了他者,代替他者去准备饭食、衣物与住处。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也必须是能够享受食物,衣着保暖,居有其所的人。他们(有时被称为“善男信女”)首先必须是能够自足的,能够享受的存在者,如此才能把将要送进口中的饭食施与别人。如此“善良”的存在状态,我们不能以落后于时代的名义,便弃之不顾。
让我们回到庄子。以佛教式的话语来说,庄子通过置身于妻子之旁,鼓盆而歌的方式,来供养妻子,来享受“死之乐”。这有异于因死而悲伤流泪,举行丧礼的社会观念。后者所打开的世界,从庄子与身故妻子间的关系来看,是遥远的世界。此时,妻子对于庄子而言,不过是为其举行丧礼的死者而已。妻子的死, 与其他的死一样,应当是在社会中有适当位置的,能够跨越的死。然而,“亲临其境”这一“供养”关系,则打开了一个与社会性观念完全不同的亲近的世界。妻子的死,在其与庄子的身体上的位置关系中,是作为“死之乐”而被享受的,是作为有价值的事物而登场的。死不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庄子与妻子的亲近关系中被共享的价值而登场。
这就是庄子告诉我们的“秘密”。也就是说,“鱼之乐”也好,“死之乐”也好,都是当“我”与他者建立深入的关系,沉浸并享受着同一个这个世界的时候,所窥见的经验。这就是作为一切社会性一侧的原—社会性的同时,又有着能够改变一切社会性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不是主体通过知觉,能动地获得的体验。走在前面的是他者,但他者在影子之中。我们能否察觉到影子之中的他者,事先是不能决定的。但是,一旦有所察觉,则亲近关系启动,“我”被析出,作为被动性经验的“鱼之乐”“死之乐” 即显现出来。
此时,“我”与他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享受“鱼之乐”“死之乐”的时候,“我”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活在一个鱼儿欢快畅游的世界,活在一个妻子死后的世界。
在本章的开头,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即使“这个我”与“这个世界”被重新组成,他者及其他世界会不会最终并未打开, 我们仍然处在只是改变了内容的自同者(与自我同一的相同事物) 闭环之中?然而,正如之后的论述所示,“这个我”与“这个世界”正是在与他者的亲近关系中而得以成立。既然如此,这就不可能是自同者的闭环,而是向他者敞开大门的同时,将“我”从自同性中解放出来的事物。
*文章摘选自“古典新读”第一辑《庄子:化鸡告时》,中岛隆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5月出版。近期我们将连续推送该系列书摘,以飨读者。转载请注明出处。
《庄子》有启迪人心的力量。各个时代的思想家都受益于庄子“打破常识,立异出新”的思考方式,它的影响跨越时间、地域,甚至专业领域,影响了一代代的思想家,每个人都能从《庄子》中获得洞察世界的方法和思考人心的快乐。本书作者从“物化”入手,“齐同”地看待万事万物,从而洞悉事物生成变化的方式,试图窥见其中蕴藏的世界的秘密,并让我更加接近一个真实的庄子。
中岛隆博,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哲学专业博士课程毕业。现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比较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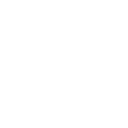

@BETHASH6